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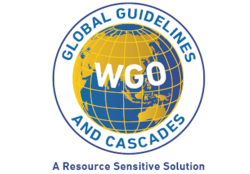
ä¸–ç•Œèƒƒè‚ ç—…å¦ç»„织全çƒæŒ‡å—
2015年8月更新


ç½—é“ è¯‘ æˆ´å® å®¡æ ¡
浙江大å¦åŒ»å¦é™¢é™„属邵逸夫医院
评阅组
Charles Bernstein (åŠ æ‹¿å¤§ï¼ˆä¸»å¸ï¼‰
Abraham Eliakim (以色列)
Suliman Fedail (è‹ä¸¹)
Michael Fried (瑞士)
Richard Gearry (新西兰)
Khean-Lee Goh (马æ¥è¥¿äºš)
Saeed Hamid (巴基斯å¦)
Aamir Ghafor Khan (巴基斯å¦)
Igor Khalif (ä¿„ç½—æ–¯)
Siew C. Ng (ä¸å›½ï¼Œé¦™æ¸¯)
Qin Ouyang (ä¸å›½)
Jean-Francois Rey (法国)
Ajit Sood (å°åº¦)
Flavio Steinwurz (巴西)
Gillian Watermeyer (å—éž)
Anton LeMair (è·å…°)

(点击展开区段)
ç‚Žç—‡æ€§è‚ ç—…ï¼ˆ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,IBD)是一组特å‘æ€§çš„æ…¢æ€§ç‚Žç—‡æ€§è‚ é“疾病。它所涵盖的两个主è¦ç–¾ç—…是克罗æ©ç—…(Crohn’s disease,CDï¼‰å’Œæºƒç–¡æ€§ç»“è‚ ç‚Žï¼ˆulcerative colitis,UC),两者的临床åŠç—…ç†ç‰¹å¾å˜åœ¨é‡å 性和异质性。
对 IBDå‘病机制的了解尚ä¸å®Œå…¨ã€‚é—ä¼ å’ŒçŽ¯å¢ƒå› ç´ ï¼Œä¾‹å¦‚è‚ é“èŒç¾¤çš„改å˜å’Œè‚ é“通é€æ€§çš„å¢žåŠ åœ¨è‚ é“å…疫失调ä¸å‘æŒ¥äº†ä½œç”¨ï¼Œå¯¼è‡´äº†èƒƒè‚ é“çš„æŸä¼¤ã€‚
CD的患病率城市高于乡æ‘,在社会ç»æµŽé«˜é˜¶å±‚ä¸æ‚£ç—…çŽ‡ä¹Ÿæ›´é«˜ã€‚å¤§éƒ¨åˆ†ç ”ç©¶æ˜¾ç¤ºï¼Œå½“å‘病率åˆå§‹ä¸Šå‡æ—¶ï¼Œå¾€å¾€æºäºŽç¤¾ä¼šç»æµŽé«˜é˜¶å±‚,但éšç€æ—¶é—´æŽ¨ç§»ç–¾ç—…å˜å¾—æ™®éå˜åœ¨ã€‚
如果个体在é’春期å‰ç§»æ°‘至å‘达国家,他原本属于低å‘病率人群,转而表现出更高的å‘病率。尤其在移民至å‘达国家的家åºç”Ÿè‚²çš„第一代人,IBDçš„å‘病率更高。
从北美洲ã€å—美洲ã€æ¬§æ´²ã€æ¾³æ´²åˆ°æ–°è¥¿å…°ï¼Œå°½ç®¡åœ°åŸŸç›¸éš”,CDå’ŒUC的表现å分相åƒï¼šCD与UC特å¾ä¸åŒï¼ŒCDç´¯åŠç»“è‚ ä»¥è¿‘ä¾§ï¼Œå¯æœ‰ä¼šé˜´ç—…å˜ã€ç˜˜ç®¡å’Œç»„织å¦ä¸Šè‚‰èŠ½è‚¿ï¼Œä¸”全层累åŠè€Œéžå±€é™äºŽç²˜è†œå±‚。在CDä¸ï¼Œè‚‰èŠ½è‚¿åœ¨åŠæ•°ä»¥ä¸Šç—…人ä¸å¯è¢«è¯å®žï¼Œç˜˜ç®¡åœ¨25%患者ä¸å˜åœ¨ã€‚
但是,东西方之间疾病ä»ç„¶å˜åœ¨å·®å¼‚。在东亚,CD在男性患者ä¸å‘ç—…çŽ‡æ›´é«˜ï¼Œå›žç»“è‚ åž‹CD比例更高,家æ—èšé›†æ€§æ›´å°‘,手术率低以åŠæ›´å°‘çš„è‚ é“外表现。与UC相关的原å‘性硬化性胆管炎(PSC)更少è§ã€‚总体上,亚洲患者需è¦æ‰‹æœ¯çš„比例较低,约在5–8%。然而,在亚洲,高比率的病例在诊æ–æ—¶å³æœ‰ç©¿é€æ€§ç—…å˜å’Œè‚›å‘¨ç—…å˜ï¼Œæ示å¤æ‚的疾病行为在东亚并éžä¸å¸¸è§[3,10–12]。
在巴基斯å¦ï¼ŒUCå’ŒCDçš„è‚ å¤–ç—…å˜æ¯”西方报é“è¦å°‘得多(在西方,如包括关节痛,25%çš„æ‚£è€…æœ‰è‚ å¤–è¡¨çŽ°ï¼‰ã€‚åœ¨å·´åŸºæ–¯å¦ï¼Œæžå°‘患者有肛周病å˜æˆ–瘘管。在å°åº¦ï¼ŒCD出现症状的年龄较西方晚åå¹´ï¼Œç»“è‚ çš„ç´¯åŠæ›´å¸¸è§ï¼Œä¸”瘘管形æˆä¼¼ä¹Žæ›´å°‘è§äº›ã€‚
ç»“æ ¸åœ¨å‘展ä¸å›½å®¶æ˜¯ä¸€ä¸ªé‰´åˆ«è¯Šæ–çš„é‡è¦é—®é¢˜ã€‚
å«IBDæ˜“æ„ŸåŸºå› çš„ä¼—å¤šåŸºå› ä½ç‚¹è¢«å‘çŽ°ã€‚å‡ ä¹Žæ‰€æœ‰è¿™äº›ä½ç‚¹çš„ç»å¯¹é£Žé™©å¹¶ä¸é«˜ï¼Œä½†å®ƒä»¬çš„å‘çŽ°å¯¹äºŽç ”å‘诊æ–æ ‡å¿—ç‰©å’Œå°†æ¥çš„治疗é¶ç‚¹è‡³å…³é‡è¦ã€‚已知会改å˜CD或UCæ˜“æ„Ÿæ€§çš„åŸºå› çªå˜åœ¨å…¨çƒä¸åŒå›½å®¶åœ°åŒºåˆ†å¸ƒä¸åŒï¼Œå°¤å…¶åœ¨æœ‰ç§æ—差异的地方[13]。NOD2çªå˜åœ¨äºšæ´²çš„ä»»ä½•ç ”ç©¶ä¸å‡æœªæŠ¥é“出现[14],而肿瘤åæ»å› å超家æ—15(TNFSF15ï¼‰åŸºå› çš„åŸºå› å¤šæ€æ€§åœ¨ä¸œäºšè¢«å‘现与CD的易感相关[15]。
IBD是一ç§æ…¢æ€§ã€åå¤å‘作的疾病。症状在å‘作时å¯ä»Žè½»åº¦åˆ°é‡åº¦ï¼Œåœ¨ç¼“解期å¯èƒ½æ¶ˆå¤±æˆ–å‡è½»ã€‚总体而言,症状å–决于累åŠè‚ é“的节段。
ä¸Žèƒƒè‚ é“ç‚Žç—‡æŸä¼¤ç›¸å…³çš„症状
è‚ é“外表现包括肌肉骨骼疾病(外周性或轴性关节炎),皮肤表现(结节性红斑ã€å疽性脓皮病),眼部表现(虹膜炎ã€å·©è†œå¤–层炎ã€è‘¡è„膜炎)和è‚胆表现(原å‘性硬化性胆管炎)。
è‚ é“并å‘ç—‡
IBD的诊æ–è¦æ±‚å®Œæ•´çš„ä½“æ ¼æ£€æŸ¥å’Œç—…å²å›žé¡¾ã€‚多ç§æ£€æŸ¥ï¼ŒåŒ…括血化验ã€ç²ªä¾¿åŒ–验ã€å†…é•œã€æ´»æ£€å’Œå½±åƒå¦æ£€æŸ¥å¸®åŠ©æŽ’é™¤å…¶ä»–ç—…å› ï¼Œå¹¶ç¡®å®šè¯Šæ–。
在内镜检查时常规å–活检。对于内镜医生æ¥è®²ï¼Œé‡è¦çš„是明确所å–çš„æ¯ä¸€å—æ´»æ£€æ ‡æœ¬éœ€è¦ç—…ç†ç§‘医生回ç”哪些特定的问题。获å–ç—…ç†æ´»æ£€æ ‡æœ¬çš„一些é‡è¦åŽŸå› 如下:
有关如何监测或治疗IBD异型增生å¯å‚è€ƒç”±ç¾Žå›½èƒƒè‚ å†…é•œå会å‘表的新共识æ„è§çš„推è[26]。新指å—推èè‰²ç´ å†…é•œä½œä¸ºé¦–é€‰çš„ç›‘æµ‹æ¨¡å¼ï¼ŒåŸºäºŽå®ƒçš„诊æ–率比éšæœºæ´»æ£€çš„æ–¹æ³•æ›´é«˜ã€‚ç„¶è€Œï¼Œè‰²ç´ å†…é•œï¼ˆç”¨æŸ“æ–™å–·æ´’ï¼‰æ˜¯å¦è¾ƒé«˜åˆ†è¾¨ç™½å…‰å†…镜更佳ä»å˜åœ¨äº‰è®®ã€‚高分辨白光内镜在识别隆起或ä¸è§„则病å˜ä¸Šæœ‰æ˜Žç¡®çš„çªç ´ã€‚在近期的éšæœºå¯¹ç…§ç ”究ä¸ï¼Œé•¿æœŸUCçš„æ‚£è€…åº”ç”¨é«˜åˆ†è¾¨è‰²ç´ å†…é•œè¾ƒé«˜åˆ†è¾¨ç™½å…‰å†…é•œå¼‚åž‹å¢žç”Ÿçš„æ£€å‡ºçŽ‡æ˜¾è‘—æ高[27],尽管å¦ä¸€é¡¹ç ”究报é“è‰²ç´ å†…é•œå’Œé«˜åˆ†è¾¨ç™½å…‰å†…é•œæ— æ˜¾è‘—å·®å¼‚[28]。
注æ„:å‡å°‘诊æ–性医疗放射暴露是很é‡è¦çš„ï¼Œå› ä¸ºæ”¾å°„æœ‰å¯¼è‡´ç™Œå˜çš„潜在风险。
æ¬§æ´²å„¿ç«¥èƒƒè‚ ç—…è‚ç—…å’Œè¥å…»å¦å会(ESPGHAN)出版了儿童和é’å°‘å¹´IBD诊æ–的修订版Portoæ ‡å‡†[34]ã€‚ä¿®è®¢ç‰ˆæ ‡å‡†åŸºäºŽåŽŸPortoæ ‡å‡†å’Œå„¿ç«¥IBD巴黎分类,并结åˆè¡€æ¸…å’Œç²ªä¾¿ç”Ÿç‰©æ ‡è®°çš„æœ€æ–°æ•°æ®ã€‚æ ‡å‡†æŽ¨è在所有怀疑IBD的儿童病例ä¸è¿›è¡Œä¸Šæ¶ˆåŒ–é“å†…é•œå’Œå›žç»“è‚ é•œæ£€æŸ¥ï¼Œå¹¶åº”ç”¨ç£å…±æŒ¯å°è‚ é€ å½±æˆ–æ— çº¿èƒ¶å›Šå†…é•œè¯„ä¼°å°è‚ 。影åƒå¦æ£€æŸ¥åœ¨å†…镜和组织å¦è¯Šæ–的典型UC病例ä¸æ˜¯ä¸å¿…è¦çš„。
1. ä½“æ ¼æ£€æŸ¥ã€‚
2. 粪便检查感染ã€ç²ªä¾¿ç™½ç»†èƒžã€‚
3. CBCã€è¡€æ¸…白蛋白。
4. 在高å±äººç¾¤ä¸HIVå’ŒTB检查—和其他机会感染ç›æŸ¥ï¼ŒHBVã€HCVã€èƒ¸ç‰‡ï¼ˆCXR)。
5. å…¨ç»“è‚ é•œæ£€æŸ¥å’Œå›žè‚ é•œæ£€æŸ¥ï¼Œå¦‚å¯è¡Œç»„织å¦åˆ†æžåˆ™å–活检。
6. 如内镜ä¸å¯èŽ·å¾—,但å¯åšé’¡å‰‚检查,那么åŒæ—¶åšå°è‚ é’¡å‰‚é€ å½±å’Œé’¡å‰‚çŒè‚ 检查。
1. ä½“æ ¼æ£€æŸ¥ã€‚
2. 粪便检查感染。
3. 粪便检查大便白细胞ã€ç²ªé’™å«è›‹ç™½ï¼ˆå¦‚内镜å¯èŽ·å–则éžå¿…须,但å¯å¸®åŠ©é€‰æ‹©è¿›ä¸€æ¥çš„检查,包括内镜)。
4. CBCã€è¡€æ¸…白蛋白ã€è¡€æ¸…é“蛋白和CRP。
5. 在高å±äººç¾¤ä¸HIVå’ŒTB检查—在已知IBD病例需接ç§ç–«è‹—治疗å‰è¡Œè¡€æ¸…å¦HAVã€HBV检查。机会感染ç›æŸ¥ï¼ŒHBVã€HCVã€VZV IgGã€èƒ¸ç‰‡ï¼ˆCXR)。
6. 如å¯èŽ·å–ï¼Œè¡Œç»“è‚ é•œæ£€æŸ¥å’Œå›žè‚ é•œæ£€æŸ¥ã€‚
7. 腹部超声扫æ。
8. 腹部CT检查。
1. ä½“æ ¼æ£€æŸ¥ã€‚
2. 粪便检查感染。
3. CBCã€è¡€æ¸…白蛋白ã€è¡€æ¸…é“蛋白和CRP。
4. 在高å±äººç¾¤ä¸HIVå’ŒTB检查—如需è¦ï¼Œåœ¨å·²çŸ¥IBD病例需接ç§ç–«è‹—治疗å‰è¡Œè¡€æ¸…å¦HAVã€HBV检查。机会感染ç›æŸ¥ï¼ŒHBVã€HCVã€VZV IgGã€èƒ¸ç‰‡ï¼ˆCXR)。
5. ç»“è‚ é•œæ£€æŸ¥å’Œå›žè‚ é•œæ£€æŸ¥ã€‚
6. 腹部超声扫æ。
7. å› ä¸ºæ— æ”¾å°„æ€§ï¼Œè…¹éƒ¨MRI 优于腹部 CT。
8. 在高TB患病率地区,下消化é“内镜检查时TBèšåˆé…¶é“¾å应(PCR)试验和培养是必è¦çš„。
9. 如果ä¸ç¡®å®šæ˜¯å¦å˜åœ¨å°è‚ ç—…å˜ï¼Œå¯è¡ŒMRIæ–层影åƒæ£€æŸ¥ï¼Œå°è‚ 胶囊内镜或CT。
10. å¦‚æžœæ€€ç–‘ç»“è‚ ç˜˜ç®¡è€Œæ–层影åƒå¦æ‰«ææ— æ³•æ˜Žç¡®æˆ–ç»“è‚ é•œæ£€ä¸å®Œæ•´ï¼Œåˆ™è¿›è¡Œé’¡çŒè‚ 。
11. 在éžå®Œæ•´ç»“è‚ é•œæ£€æŸ¥æƒ…å†µä¸‹ï¼Œå¯ä¼˜é€‰CTç»“è‚ é€ å½±æ£€æŸ¥æ•´ä¸ªç»“è‚ ã€‚ä¸€äº›æ”¾å°„ç§‘å¯¹CD患者进行CTç»“è‚ é€ å½±æŒä¿ç•™æ„è§ã€‚ç»“è‚ èƒ¶å›Šé•œå¯ä½œä¸ºéžå®Œå…¨ç»“è‚ é•œæ£€æŸ¥çš„å¦ä¸€ç§æ›¿ä»£é€‰æ‹©ï¼Œé™¤éžå·²çŸ¥æˆ–é«˜åº¦æ€€ç–‘ç»“è‚ ç‹çª„。
12. 如果克罗æ©ç—…的诊æ–ä»ç„¶ä¸æ˜Žç¡®ï¼Œè¿›è¡Œèƒ¶å›Šå†…镜检查。
13. 如累åŠä¸æ®µå°è‚ å¯è¡ŒåŒæ°”囊å°è‚ 镜(顺行性或逆行性,å–决于怀疑部ä½ï¼‰
å‘患者æ供关于疾病的解释和个人情况很é‡è¦ã€‚鼓励患者积æžåœ°å‚与决ç–。
IBD处ç†é€šå¸¸éœ€è¦é•¿æœŸè”åˆè¯ç‰©æ²»ç–—以控制疾病。医生应该清楚è¯ç‰©å¯èƒ½çš„相互作用和副作用。通常,患者会需è¦æ‰‹æœ¯ï¼Œè¿™å°±è¦æ±‚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紧密åˆä½œæ¥ä¼˜åŒ–患者的治疗。
IBD处ç†åº”基于:
æ²»ç–—çš„ç›®æ ‡æ˜¯ï¼š
膳食和生活方å¼çš„考虑:
钙调磷酸酶抑制剂ä¿ç•™ç”¨äºŽç‰¹æ®Šæƒ…况。
IBD 患者å¯èƒ½å› 手术或è¯ç‰©éš¾æ²»æ€§ç—…å˜éœ€è¦ä½é™¢—这至少å IBDç›´æŽ¥é€ æˆè´¹ç”¨çš„一åŠã€‚
UC的手术治疗
硫唑嘌呤:
围手术期应用英夫利昔å•æŠ—ã€é˜¿è¾¾æœ¨å•æŠ—或西妥ç å•æŠ—ç‰æŠ—-TNF-α治疗:
1. 在阿米巴æµè¡Œåœ°åŒºï¼Œå½“诊æ–资æºæœ‰é™æ—¶ï¼Œåº”用一个疗程的抗阿米巴治疗。
2. 柳氮磺胺å¡å•¶ï¼ˆæœ€ä¾¿å®œï¼‰ç”¨äºŽæ²»ç–—所有轻ä¸åº¦ç»“è‚ ç‚Žå’Œç»´æŒç¼“解。ä¸åŒçš„美沙拉嗪制剂å¯ä¾›é€‰ç”¨ï¼ŒåŒ…括Asacol 800 mgã€Lialda (美国) 〠Mezavant (欧洲) 1200 mg 片剂和 Pentasa 2 g 袋装。这些较大的æ¯æ—¥ä¸€æ¬¡çš„剂é‡æœ‰åŠ©äºŽæ›´å¥½çš„ä¾ä»Žæ€§ï¼Œè€Œä¸”æ— ç£ºèƒºç±»å‰¯ä½œç”¨ã€‚
3. æ¿€ç´ çŒè‚ 剂(尤其是泡沫载体的,比液体çŒè‚ 剂更容易ä¿ç•™ï¼Œç”¨äºŽè¿œç«¯ç»“è‚ ç—…å˜ï¼‰ã€‚æ¿€ç´ çŒè‚ 剂有时å¯ç”¨å½“地å¯èŽ·å¾—资æºåˆ¶ä½œï¼Œæ•…有时æˆæœ¬è¾ƒä½Žã€‚
4. å£æœæ³¼å°¼æ¾ç”¨äºŽæ²»ç–—ä¸é‡åº¦ç–¾ç—…(急性é‡ç—‡ç–¾ç—…需è¦é™è„‰ä½¿ç”¨æ¿€ç´ )。
5. 如果急性é‡ç—‡ç»“è‚ ç‚Žå¯¹é™è„‰æ¿€ç´ æ— åº”ç”æˆ–æ‚£è€…æœ‰æ…¢æ€§æ¿€ç´ æŠµæŠ—æ€§æˆ–æ¿€ç´ ä¾èµ–æ€§ç»“è‚ ç‚Žï¼Œè€ƒè™‘ç»“è‚ åˆ‡é™¤æœ¯ã€‚åœ¨æ€¥æ€§é‡ç—‡æºƒç–¡æ€§ç»“è‚ ç‚Žä¸éœ€è¦åŠæ—¶åšå‡ºæ‰‹æœ¯çš„决定。在é™è„‰ä½¿ç”¨æ¿€ç´ 的第3天考虑Oxford 或 Swedenç»“å±€é¢„æµ‹æŒ‡æ ‡ã€‚
6. 在难治性疾病ä¸éœ€è¦ç§¯æžå¯»æ‰¾CMV和艰难æ¢çŠ¶èŠ½èƒžæ†èŒã€‚
7. ç¡«å”‘å˜Œå‘¤ç”¨äºŽæ¿€ç´ ä¾èµ–者。如果没有硫唑嘌呤或患者ä¸è€å—,å¯ä»¥è€ƒè™‘甲氨è¶å‘¤ï¼Œä½†è¿™åœ¨UCä¸æœªè¢«è¯å®žã€‚
1. 柳氮磺胺å¡å•¶å¯è¢«ç”¨äºŽè½»ä¸åº¦ç»“è‚ ç‚Žã€‚
2. Asacol 800 mg,Lialda/Mezavant 1200 mg 片剂和Pentasa 2 g 袋装目å‰å¯èŽ·å–,有助于更好的ä¾ä»Žæ€§ï¼Œä¸”æ— ç£ºèƒºç±»å‰¯ä½œç”¨ã€‚
3. 5-ASA çŒè‚ å‰‚æˆ–æ “å‰‚ç”¨äºŽè¿œç«¯ç—…å˜ã€‚它们å¯ä»£æ›¿å£æœ5-ASA用于远端病å˜çš„ç»´æŒç¼“è§£ã€‚æ¿€ç´ çŒè‚ 剂也是一ç§é€‰æ‹©ï¼Œä½†é€šå¸¸å¹¶ä¸ç”¨äºŽç»´æŒæ²»ç–—。
4. å£æœå’Œç›´è‚ 5-ASAè”åˆç–—法在活动性远端病å˜ç”šè‡³æ´»åŠ¨æ€§å…¨ç»“è‚ ç‚Žä¸å¯èƒ½æ›´æœ‰æ•ˆã€‚
5. 如果使用5-ASAç»´æŒç¼“解失败,那么考虑硫唑嘌呤或6-MP/AZA;如果硫唑嘌呤失败,则考虑抗-TNF或维多ç å•æŠ—。
6. 如果生物制剂å¯èŽ·å¾—,那么å–决于疾病严é‡ç¨‹åº¦ï¼Œå¯åº”用生物制剂æ¥å–代å…疫调节剂å•è¯æ²»ç–—。
1. 在急性é‡ç—‡ç»“è‚ ç‚Žæ‚£è€…ä¸å¯ä»¥è€ƒè™‘环å¢ç´ 。
2. 英夫利昔å•æŠ—å¯è€ƒè™‘用于急性é‡ç—‡ç»“è‚ ç‚Žæˆ–ä¸é‡åº¦æ¿€ç´ ä¾èµ–æˆ–æ¿€ç´ æŠµæŠ—æ€§ç»“è‚ ç‚Ž—用阿达木å•æŠ—也å¯ä»¥ã€‚
3. 英夫利昔å•æŠ—或维多ç å•æŠ—é™è„‰æ³¨å°„,或Humira(阿达木å•æŠ—)或戈利木å•æŠ—皮下注射,是ä¸é‡åº¦é—¨è¯Šç—…人的选择。
4. 硫唑嘌呤或6-MP —硫唑嘌呤失败的病例,需考虑抗TNF或维多ç å•æŠ—。
1. 在阿米巴æµè¡Œåœ°åŒºï¼Œå½“诊æ–资æºæœ‰é™æ—¶ï¼Œåº”用一个疗程的抗阿米巴治疗。
2. åœ¨ç»“æ ¸æµè¡Œåœ°åŒºï¼Œè€ƒè™‘给予2-3ä¸ªæœˆçš„æŠ—ç»“æ ¸è¯•éªŒæ€§æ²»ç–—æ¥åˆ¤æ–患者的治疗å应。
3. 柳氮磺胺å¡å•¶ï¼ˆæœ€ä¾¿å®œï¼‰ç”¨äºŽæ²»ç–—所有轻ä¸åº¦ç»“è‚ ç‚Žå’Œç»´æŒç¼“解。
4. æ¿€ç´ çŒè‚ å‰‚ç”¨äºŽè¿œç«¯ç»“è‚ ç—…å˜ã€‚æ¿€ç´ çŒè‚ 剂有时å¯ç”¨å½“地å¯èŽ·å–资æºåˆ¶ä½œï¼Œæ•…有时æˆæœ¬è¾ƒä½Žã€‚
5. å¯¹å›žç»“è‚ æˆ–ç»“è‚ ç—…å˜å°è¯•ä½¿ç”¨ç”²ç¡å”‘。
6. å£æœæ³¼å°¼æ¾ç”¨äºŽä¸é‡åº¦ç–¾ç—…。
7. 如果有一çŸæ®µçš„å°è‚ ç—…å˜ï¼Œåº”考虑手术。
8. 硫唑嘌呤或甲氨è¶å‘¤ã€‚
9. 甲ç¡å”‘åœ¨å›žè‚ åˆ‡é™¤åŠä¸€æœŸå›žç»“è‚ å»åˆæœ¯åŽçŸæœŸï¼ˆ3月)维æŒæ²»ç–—。
1. 诊æ–并首先治疗TB和寄生虫。
2. 柳氮磺胺å¡å•¶æ²»ç–—è½»ä¸åº¦æ´»åŠ¨æ€§ç»“è‚ ç‚Žçš„CD。
3. 布地奈德å¯ç”¨äºŽè½»åº¦å›žè‚ æˆ–å›žç»“è‚ ç—…å˜ï¼ˆå³åŠç»“è‚ ï¼‰ã€‚
4. å¦‚æžœä¸€ä¸ªæ¿€ç´ ç–—ç¨‹åŽæœªè¾¾ç¼“解,或CDä¸è‰¯é¢„åŽçš„å› åå˜åœ¨ï¼Œé‚£ä¹ˆè€ƒè™‘硫唑嘌呤(或6-MP/AZA);在硫唑嘌呤失败的患者ä¸ï¼Œè€ƒè™‘甲氨è¶å‘¤ã€‚抗-TNF也å¯è¢«è€ƒè™‘å–代AZA/6-MP或MTX,且这些è¯ç‰©è”åˆåº”用å¯ä¼˜åŒ–疗效(如AZA/6-MP +英夫利昔å•æŠ—疗效已被è¯å®žï¼‰ã€‚
5. 治疗的è¯ç‰©æµ“度和抗-TNF抗体水平监测å¯æŒ‡å¯¼æ²»ç–—,尤其在继å‘失应ç”æˆ–å› é•¿ç¨‹ç¼“è§£æƒ³è¦è€ƒè™‘è¯ç‰©å‡é‡çš„情况。
1. 英夫利昔å•æŠ—ã€é˜¿è¾¾æœ¨å•æŠ—或西妥ç å•æŠ—å¯è€ƒè™‘用于ä¸é‡åº¦æ¿€ç´ ä¾èµ–æˆ–æ¿€ç´ æŠµæŠ—æ€§çš„ç–¾ç—…ã€‚
2. å…疫抑制è¯ç‰©ï¼Œå¦‚6-MP å’ŒAZA,在治疗CD瘘管ä¸ä¹Ÿéžå¸¸æœ‰ç”¨ã€‚这些è¯ç‰©è¢«è¯å®žå¯å¢žå¼ºè‹±å¤«åˆ©æ˜”å•æŠ—的应ç”,且å¯ä¸Žå…¶ä»–抗-TNFåŒæ—¶ä½¿ç”¨æ¥å‡å°‘它们的å…疫原性。
3. 抗-TNF失败时å¯è€ƒè™‘应用维多ç å•æŠ—。
4. 生物制剂的治疗è¯ç‰©ç›‘测如上述。
1. 甲ç¡å”‘。
2. 如å˜åœ¨è„“肿,进行手术。
3. 环丙沙星。
4. 甲ç¡å”‘和环丙沙星è”åˆç”¨è¯ã€‚如果长期è€å—ï¼Œè¿™äº›æŠ—ç”Ÿç´ å¯é—´æ‡åº”用作为瘘管é—åˆçš„ç»´æŒæ²»ç–—。
5. 手术—应早期考虑,且如果需è¦é•¿æœŸæŠ—ç”Ÿç´ ç»´æŒæ²»ç–—。
6. è¯ç‰©å’Œæ‰‹æœ¯è”åˆæ²»ç–—æ供最佳预åŽã€‚
1. 甲ç¡å”‘。
2. 如å˜åœ¨è„“肿,进行手术。
3. 环丙沙星。
4. 甲ç¡å”‘和环丙沙星è”åˆç”¨è¯ã€‚如果长期è€å—ï¼Œè¿™äº›æŠ—ç”Ÿç´ å¯ç”¨äºŽç˜˜ç®¡é—åˆçš„ç»´æŒæ²»ç–—。
5. 手术—应早期考虑,且如果需è¦é•¿æœŸæŠ—ç”Ÿç´ ç»´æŒæ²»ç–—。
6. AZA/6-MP用于瘘管é—åˆçš„ç»´æŒæ²»ç–—(长期é—åˆçŽ‡ä¸é«˜ï¼‰ã€‚
1. 甲ç¡å”‘。
2. 如å˜åœ¨è„“肿,进行手术(麻醉下检查并挂线)。
3. 环丙沙星。
4. 甲ç¡å”‘和环丙沙星è”åˆæ²»ç–—。如果长期è€å—ï¼Œè¿™äº›æŠ—ç”Ÿç´ å¯ç”¨äºŽç˜˜ç®¡é—åˆçš„ç»´æŒæ²»ç–—。
5. 手术—应早期考虑,且如果需è¦é•¿æœŸæŠ—ç”Ÿç´ ç»´æŒæ²»ç–—,且尤其是å•çº¯æ€§ç˜˜ç®¡ã€‚
6. AZA/6-MP用于瘘管é—åˆçš„ç»´æŒæ²»ç–—。
7. 英夫利æ¯å•æŠ—。
8. 阿达木å•æŠ—用于英夫利æ¯å•æŠ—治疗失败者,或作为英夫利æ¯çš„首选替代è¯ç‰©ã€‚
9. 手术治疗å¤æ‚性瘘管。